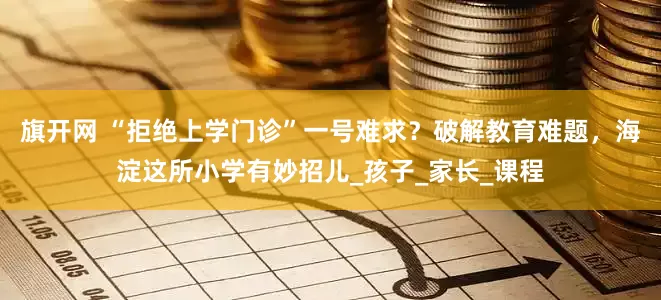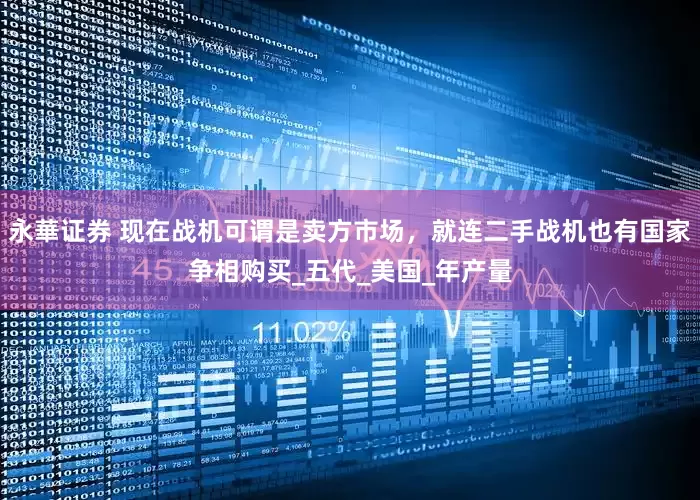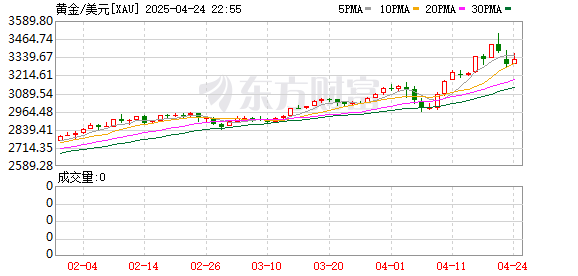当前,在脑部疾病的治疗中,血脑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BBB)如同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卡”创利配资,将大多数药物阻隔于脑外,极大限制了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疾病的治疗。传统破局手段 —— 脑室手术给药,虽能绕过 BBB 直达病灶,却因高昂的医疗成本、严苛的操作门槛以及不可忽视的手术风险(如感染、出血、神经损伤),始终难以成为普适方案。鼻-脑递送技术另辟蹊径,为药物入脑开辟了“绿色通道”,该技术巧妙利用鼻腔与脑之间独特的解剖与生理通路,直接将药物递送至脑实质,绕过 BBB 及肝脏首过代谢,以非侵入、无痛的方式,从“突破屏障”转向“借道而行”。这一技术革新不仅为脑部疾病治疗提供了新范式,也开启精准脑靶向治疗的新纪元。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整体的结构与功能会逐渐退化,身体对各类刺激的响应与适应性调节也会大打折扣,随之包括神经退行性疾病、脑血管疾病和神经精神疾病在内的 CNS 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 给社会和医疗系统带来了沉重负担。受脑部疾病的复杂性与生理屏障的限制,目前大多数脑部疾病仍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图1):一方面, BBB 和血脑脊液屏障(Blood Cerebrospinal Fluid Barrier, BCSFB)构成天然防线,能够有效阻挡有毒物质渗透,但也导致约98%的治疗药物难以进入 CNS,限制了药物在脑部的有效作用[1];另一方面,脑部病灶的药物浓度是影响疗效的重要因素,常规全身给药时,药物靶向蓄积能力不足,会无差别地作用于病灶和正常组织,不仅削弱治疗效果,还可能引发严重毒性和不良反应[2]。
展开剩余95%图1. 药物进入 CNS 所面临的各种挑战[3]
鼻-脑给药( Nose-to-Brain ,N2B),作为一种直接靶向大脑的给药途径,在 CNS 疾病的药物治疗中展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文系统阐述了经鼻-脑给药后药物进入CNS的机制、优势、应用及发展前景,以及非临床研究的关注点和面临的挑战,旨在推动突破血脑屏障的高效递送策略探索,加速 CNS 药物非临床开发。
01 鼻-脑给药的优势在 CNS 药物的研发中,给药途径的选择至关重要。目前,常见的给药途径有静脉注射、口服给药和鼻内给药(图2)[4]。
口服给药是主流途径,虽具备便捷性优势,但其在 CNS 疾病治疗中面临双重生物屏障限制。
其一是经胃肠道吸收的药物需通过门静脉进入肝脏代谢,受首过效应影响,有部分活性成分被酶解失活,显著降低系统循环中的生物利用度;其二是残留药物需进一步突破由内皮细胞、基底膜及星形胶质细胞构成的 BBB ,其通过主动外排转运和物理孔径限制,导致约 98% 的小分子药物及几乎所有大分子治疗药物(如抗体、基因载体)无法有效浸润脑实质。
这种药代动力学的级联衰减效应,使得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 CSF)中的药物浓度常低于最低有效治疗阈值(Minimum Effective Dose Threshold, MET),严重制约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 CNS 疾病的干预效果[5]。
图2. 三种给药途径的比较[4](A 静脉给药,B 口服给药,C 鼻内给药)
鼻-脑给药作为 CNS 靶向治疗的重要突破,兼具系统给药和局部给药的优势,其核心优势有精准靶向、起效快、低全身副作用[6]。
药物可直接通过鼻腔黏膜嗅神经与三叉神经通路实现神经轴突旁路转运,使药物绕过 BBB 直接递送至嗅球、CSF 及脑实质靶区(如海马体、黑质等与疾病相关的部位),实现脑组织靶向局部治疗,提高药物在 CNS 的生物利用度;其次鼻腔黏膜下血管丰富,且药物可通过鼻-脑通路直接进入 CNS,无需经过胃肠道吸收、肝脏首过代谢和全身血液循环的延迟,起效速度快,适合急性脑损伤、脑卒中、癫痫发作等需要快速起效的 CNS 急症的治疗[7],如外泌体经鼻给药后 1 h 抵达脑损伤区,24 h 内持续积累,快速抑制小胶质细胞炎症[8];此外,naojiye 给药无需注射或手术,患者通过鼻喷/滴注等方式自行给药,降低感染和操作并发症风险,可规避口服导致的严重胃肠道反应[9]。
02 鼻-脑给药的递送机制1、鼻至 CNS 的生理学基础
鼻腔的独特结构和功能使其成为天然的高效脑靶向给药的门户。在人类鼻腔中,主要分为前庭区、呼吸区、嗅觉区。其中药物在鼻内的吸收主要发生在呼吸区和嗅觉区[2]。
前庭区,由鳞状上皮细胞组成,在药物吸收/摄取中无重要作用; 呼吸区,由位于前庭后方的呼吸道上皮组成,药物通过呼吸道上皮吸收可沉积到固有层,并沿着三叉神经分支进入大脑,药物也可在神经元内或在神经周围和血管周围分布,通过三叉神经节和脑干进入大脑; 嗅觉区,由位于鼻腔的后背侧的嗅觉上皮组成,是鼻-脑给药关键的解剖区域。嗅觉区有大量嗅觉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将纤毛送入鼻腔腔内,药物可以被嗅觉受体吸收,也可以通过固有层内的跨细胞或神经周围/血管周围途径穿过嗅上皮进入嗅球,从嗅球进入大脑(图3)[10]。图3. 鼻-脑的生理结构[10]
鼻腔与 CNS 的生理学连接主要通过三条核心通路实现(图4)[11] :
嗅觉通路的直接神经连接:筛骨的多孔筛板允许嗅觉神经元轴突(直径约 0.2 μm)穿过并进入颅内嗅球,形成嗅觉神经,为药物提供直接入脑通道;同时,药物可通过嗅觉上皮细胞间较松散的紧密连接(旁细胞途径)进入神经周围间隙,最终扩散至 CSF。 三叉神经的广泛支配:三叉神经分支密集分布于鼻腔黏膜,药物经其末梢摄取后,通过轴突逆向运输至三叉神经节或脑干核团,进而分布至全脑。 CSF 与淋巴系统的协同作用:药物经嗅神经或三叉神经旁路进入 CSF 后,可随脑室系统(如侧脑室、第四脑室)循环扩散至脑实质。此外,鼻腔黏膜中的相关淋巴组织(NALT)通过淋巴-CNS 交互调节药物递送,进一步增强脑靶向的效率。
图4. 鼻-脑给药的传递途径[10]
2、鼻内给药至 CNS 的递送路径
从鼻腔到大脑区域的药物递送主要通过嗅觉和三叉神经元的神经元通路(以嗅觉为主),次要途径是使用 CSF、淋巴系统和血管吸收(图5)。鼻腔嗅觉区域的嗅上皮是药物入脑的起始界面,当药物接触嗅上皮表面时,需先通过嗅细胞的纤毛或细胞膜,经跨细胞转运或细胞间通道穿过嗅上皮,进入其下方的固有层;固有层内富含嗅神经束和嗅鞘细胞,药物在固有层中可通过两种途径向脑内递送:
一是被嗅鞘细胞包裹的嗅神经束作为“通道“(经鼻入脑的主要直接途径),随轴突运输方向穿过筛板(筛骨的多孔结构,分隔鼻腔与颅腔,是嗅神经进入颅腔的通道);
二是通过固有层的血管或淋巴间接扩散;穿过筛板后,药物进入颅腔,先接触蛛网膜下腔的CSF,或直接作用于邻近的脑组织。进入 CSF 的药物会随 CSF 循环扩散,与脑组织的间质液混合,再通过血管周间隙进一步转运至大脑各区域,最终遍及CNS[12]。
图5. “鼻-脑”递送的主要机制通路[12]
(A 表示鼻腔内部结构示意图及鼻-脑给药的三种途径;B 表示嗅觉上皮和固有层的各主要组成部分创利配资,及鼻腔-脑的吸收路径。)
根据药物分子的类型,细胞转运过程涉及胞外和胞内两种转运方式(图5)[11][12]。
细胞内/神经内转运:药物通过受体介导的胞吞作用或非特异性胞饮从嗅上皮的嗅细胞或三叉神经的感觉神经末梢的细胞膜(嗅上皮及三叉神经)进入神经细胞,经轴突运输和跨突触传递向 CNS 迁移。 细胞外转运:药物通过细胞旁路从鼻上皮细胞间的紧密连接进入黏膜下固有层的细胞间隙,沿着嗅神经束周围的细胞外间隙和 CSF 扩散至到 CNS。胞内转运适用于小分子脂溶性药物、病毒,胞外转运则适用于水溶性小分子、纳米粒、多肽;细胞内运输途径比细胞外路径缓慢,需要数小时至数天才能扩散至 CNS 的不同区域,而胞外转运扩散较快,仅需数分钟至数小时,但胞内转运的脑靶向性较高,且受溶酶体保护,酶降解风险低[13]。
3、鼻-脑给药的应用
目前已获 FDA 批准上市的 CNS 疾病类的鼻喷制剂约 16 款[14],主要集中于疼痛、偏头痛、抑郁、癫痫、阿片类药物过量等疾病领域(表1)。随着鼻腔-脑通路机制研究的深入、精密喷雾泵及微粒工程技术的进步,以及血脑屏障穿透策略的多样化,靶向 CNS 的鼻喷制剂正呈现出“精准递送+对因治疗”双轮驱动的发展趋势。
表1. FDA 批准上市的 CNS 类的鼻喷制剂
03 鼻-脑给药非临床研究关注点1、鼻-脑给药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的一般考虑
目前 CDE、ICH、FDA 和 EMA 均无专门针对鼻-脑给药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的相关指导原则。
根据药物类型,可以参考通用的指导原则,如按照新分子实体申报参考 ICH M3(R2)、ICH S6(R1) 的指导原则;对于改良型药物,FDA《改变制剂处方和变更给药途径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技术指导原则》中推荐拟用途径开展单次和/或重复给药毒性试验,包括完全的组织病理学检查,其中短期研究(2~4 周)应包括 2 个种属,包括至少 1 种非啮齿类,在最相关种属中进行长期(可达 6 个月)研究,具体给药时间一般遵循 ICH M3 或 ICH S9 的建议。
作为新分子实体药物(New Molecular Entity,NME)申报,其完整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应涵盖药效学、药代动力学(ADME)、一般毒性(通常两个种属)、安全药理学(核心组合:心血管、呼吸、中枢神经系统)、局部毒性(刺激性、过敏性等)以及特殊毒性(遗传毒性、生殖毒性、致癌性),并需同时关注局部和全身毒性反应。 作为改良型药物申报,给药途径变更可能会影响制剂处方、PK/ADME 特性及新途径相关毒性,进而影响药品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为评估风险,关键需开展新给药途径与原途径的全面 PK/ADME 的比对研究。如现有全身毒性信息不足或新途径下的全身暴露水平(如暴露量、达峰时间、组织分布)发生显著变化,需补充附加毒性试验(包含安全药理学和生殖毒性试验);如现有全身毒性信息能充分支持新途径的暴露情况,可基于现有数据进行桥接评估。对于需长期使用的药物,还应考虑补充致癌性试验[15]。2、鼻-脑给药非临床评价的关注点
鼻-脑给药有很多优势,但也有很多局限,药物靶向递送受多种因素影响,生理环境、药物理化性质、制剂相关、试验方式等因素对鼻内药物的吸收都会产生影响(表2),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彼此关联,构成了复杂的影响网络;在开展鼻-脑给药的非临床评价时应关注制剂、鼻腔的种属差异、给药设计、特殊毒性考察和安全范围等[16]。
表2. 影响鼻内给药递送 CNS 的因素
(1) 制剂相关因素
药物的渗透性和稳定性影响鼻-脑给药的吸收和功效,其中鼻黏液层渗透、鼻黏膜转运和脑内递送都会影响活性成分的吸收。考虑到药物对鼻黏膜和纤毛的潜在毒性、局部炎症反应风险以及外来物质进入脑组织可能引起的不良免疫反应和安全问题[17],药物本身的安全性是重中之重,同时还要考虑制剂中除药物外的活性成分和辅料的安全性。在非临床研究中应采用与临床试验或上市产品一致的处方进行研究,以真实地反映受试物的制剂特征,最大程度地增加非临床研究结果到临床外推的可行性。如Zavegepant鼻喷剂(商品名:Zavzpret)在非临床研究与临床研究阶段使用的制剂在核心成分、给药途径和剂量设计上基本一致,且具有良好的水溶性和氧化稳定性,易于鼻内输送。
(2) 鼻腔的种属差异
尽管哺乳动物鼻腔的解剖结构与生理功能具有基本相似性,但在鼻腔给药研究及毒理学结果解读中,必须充分考虑种属间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同种属内的鼻腔表面积变异,如实验动物(如大鼠、小鼠)的鼻腔表面积随年龄、体重增长而变化,可能影响局部药物暴露量的计算与剂量标准化; 另一方面是种属间鼻腔功能区占比差异,不同种属的鼻腔功能区分布与其生存需求密切相关(表3)[2],如人与猴的鼻腔以呼吸功能主导,呼吸区占比高,嗅区相对较小,而犬、兔及啮齿类动物(大鼠、小鼠)的鼻腔兼具呼吸与高度发达的嗅觉功能,嗅区面积显著扩大(如大鼠嗅区占鼻腔总面积40-50%,而人仅占约 3%),且这些动物鼻甲结构更复杂,以支持觅食、天敌防御等生存行为。因此创利配资,非临床研究中,在进行局部毒性评估中,嗅区占比大的种属(如大鼠)可能对药物刺激更敏感,需重点考察嗅上皮损伤;在全身暴露推算中,呼吸区与嗅区的吸收效率差异可能影响跨种属外推,需结合功能区表面积校正剂量;对于嗅觉依赖型种属的药物暴露可能因气味厌恶影响摄食或应激反应,需在试验设计中予以控制,排除行为学干扰。
表3. 不同种属鼻腔表面积与给药体积参数表[16]
注:†表面积比值 = 动物鼻表面积 / 人鼻表面积(160 cm²),用于局部剂量校正;儿童鼻腔表面积约为成人1/3(3岁约50 cm²),最大安全体积≤50 μL/侧
(3) 给药设计
鼻内给药剂量受限于鼻腔体积的大小的影响,当给药体积过大时会有药物入肺的风险。故在有限的给药体积下,可通过调整给药频次、药物浓度来获得合适的给药剂量(表4),大体积剂量也可分次给予双侧鼻孔进行给药(如大鼠给药 50 µL可分为双侧 25µL给药)。不同种属动物鼻腔的给药体积不同,其中大鼠给药体积约为 10~50µL/只·侧,犬的给药体积约为 100~200µL/只·侧,猴的给药体积约为 12~30µL/kg·侧,而人的给药体积 ≤500 µL /只·侧。
表4. 鼻内给药中不同给药形式
因此,在非临床评价中应增加肺部暴露的预防性监测(如病理学检查中增加肺组织切片),药代动力学研究中检测肺组织药物浓度(如超出鼻腔剂量5%提示渗漏)[18];在进行局部耐受性评估时,对于高浓度/高频次给药,增加鼻黏膜病理评分频次(如给药第7、28天);扫描电镜观察纤毛完整性等[19]。在剂量标准化设计时,按鼻腔表面积来校正剂量(如大鼠剂量=人剂量×(大鼠鼻表面积/人鼻表面积))(表3)。
(4) 特殊毒性考察
鼻内给药试验中应结合鼻腔的主要特征关注呼吸、神经和免疫等毒性变化[16]。
在呼吸方面,药物体积过大、纤毛清除抑制、麻醉等情况均可能增加肺部分布和暴露,因此毒理学研究中应关注鼻腔的组织病理学评估,以及药物暴露于口咽、喉、气管、肺等组织的病理改变,如果“下颌下淋巴结(或颏下淋巴结)、支气管肺淋巴结及纵隔淋巴结肿大,也要进行相应评估。其次,还应考察的辅料组和活性成分的呼吸道毒性。
在中枢神经方面,鼻-脑给药可绕过 BBB 来提高药物在 CNS 的暴露,但同步也会放大中枢毒性风险。因此,在毒理学研究中,通常在重复给药毒性试验中伴随神经功能的监测(如伴随安全药理学)来评估神经毒性。如艾司氯胺酮鼻喷剂(商品名Spravato)在啮齿类动物的重复给药毒性试验中进行行为学指标的考察,包括行为活动、学习记忆、神经反射等神经功能指标;如 Zavegepant 药物在大鼠中重复给药试验中整合水迷宫测试,并在猴重复试验中增加 CSF 检测显示 CSF/Plasma Ratio<0.05,证实中枢暴露极低。
在免疫方面,鼻腔内包含大量的鼻黏膜,是黏膜免疫的重要场所之一,与外部反复接触易产生局部的免疫反应,引起局部组织的损伤和临近组织的免疫反应。因此应关注免疫毒性和消化道毒性,大分子药物(如多肽、蛋白质等)反复接触鼻腔黏膜,容易引起固有免疫反应以及由免疫球蛋白E(IgE)介导的I型超敏反应。
(5) 安全范围
安全范围是药物未观察到不良反应剂量(NOAEL)和人体有效剂量之间的比值,该值越大,安全性越高。
鼻腔给药的安全性包括两部分,即全身系统安全性和鼻腔局部安全性。种属外推方法如下表(表5),但鼻腔体积与表面积并非恒定的生理参数,其会随年龄、体重增长发生显著变化,且同种动物的不同品系间也存在较大差异。这一特性会导致长周期试验中,首次与末次给药的单位剂量出现明显偏差。如艾司氯胺酮鼻喷剂在大鼠重复给药毒性试验中(尤其是神经毒性评估)因未依据大鼠实时体重校准给药剂量,结果的可靠性受到监管部门质疑[16]。
鉴于此,在表征局部给药剂量时,建议引入鼻腔表面积/体积与年龄的关联关系进行剂量换算,以此更精准地量化鼻腔给药的实际剂量,减少因生理参数动态变化对试验结果产生的干扰。
表5. 鼻内给药中安全范围的计算
04 进展和挑战鼻内给药因非侵入性、操作便捷及潜在高效直达 CNS 的特点,仍是治疗 CNS 疾病的前沿策略。为突破 BBB 的限制,越来越多先进材料与技术被研发应用,旨在增强 CNS 疾病治疗中药物的脑靶向递送效率。目前研究通过采用被动和/或主动策略,以可控、非侵入的方式实现 BBB 的调节与穿透,进而设计出多种药物递送系统,用于精准递送各类治疗药物,包括小分子药物、蛋白质、基因药物及其他生物制剂[20]。鉴于对递送效率与安全性的要求,多数可穿透 BBB 的药物递送系统均采用纳米级设计,且具备定制化的化学成分与表面性质(图6)。
图6. 鼻-脑给药递送的纳米颗粒系统[22]
鼻内给药虽有许多优势,但实现鼻-脑给药仍面临多重挑战[7][17] [21]:
生理方面,复杂的鼻腔结构和几何形状(如难以精确沉积药物至嗅区的面积)、鼻黏膜纤毛清除、局部血液循环和酶降解作用、以及鼻炎/鼻塞等病理状态均阻碍药物吸收并导致个体差异;
制剂方面,有限的给药体积和吸收表面积限制了药物递送效率,尤其对大分子药物,虽可添加吸收促进剂以提高生物利用度和黏膜滞留,但其对鼻纤毛的毒性及潜在黏膜损伤风险需严格评估,辅料选择也需全面的毒理学评价;
临床方面,支持鼻内给药途径仍面临安全性和药物吸收的问题,且用于治疗 CNS 疾病有效性的临床终点证据尚不充分。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鼻内给药,特别是用于 CNS 疾病治疗的障碍。
05 结语鼻-脑给药为靶向治疗 CNS 疾病带来新的思路,可绕过血脑屏障实现药物快速吸收,但药物的疗效和安全仍受多种变量的影响,因此在非临床研究中必须跳出常规给药的框架,关注鼻-脑给药途径的特殊结构、评价体系以及临床转化。鼻内给药制剂在 CNS 疾病领域的爆发式增长,本质是“时效性”和“可及性”的双重革新。未来随着吸收增强技术的普适化及神经靶向递送系统的成熟,鼻-脑给药有望开启 CNS 治疗的“鼻腔时代”。
鼎泰集团TriApex 聚焦 CNS 专病领域,致力于通过技术突破打破传统给药途径的体系壁垒。目前,集团已完成多项鼻内给药相关的药效学与毒理学试验,积累了丰富的给药操作经验,实验种属属覆盖全年龄段的大小鼠、非人灵长类动物(NHPs)及犬等种属。依托鼻内给药与 CNS 治疗的深度结合,鼎泰集团正不断夯实其在 CNS 药物开发领域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凭借对创新技术的持续投入和卓越的技术服务能力,为全球新药研发注入强劲动能。
参考资料:
[1] Deng CX. Targeted drug delivery across the blood-brain barrier using ultrasound technique. Ther Deliv. 2010 Dec;1(6):819-48. doi: 10.4155/tde.10.66. PMID: 21785679; PMCID: PMC3140134.
[2] Lochhead JJ, Thorne RG. Intranasal delivery of biologics to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dv Drug Deliv Rev. 2012 May 15;64(7):614-28. doi: 10.1016/j.addr.2011.11.002. Epub 2011 Nov 15. PMID: 22119441.
[3] Li C, Yao S, Li Z, Gao Y. Application of Novel Drug-Delivery Strategies in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dv Mater. 2025 Jun 9:e2503646. doi: 10.1002/adma.202503646.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489094.
[4] Wang R, Zhang Y, Guo Y, Zeng W, Li J, Wu J, Li N, Zhu A, Li J, Di L, Cao P. Plant-derived nanovesicles: Promising therapeutics and drug delivery nanoplatforms for brain disorders. Fundam Res. 2023 Dec 5;5(2):830-850. doi: 10.1016/j.fmre.2023.09.007. PMID: 40242551; PMCID: PMC11997602.
[5] Lou J, Duan H, Qin Q, Teng Z, Gan F, Zhou X, Zhou X. Advances in Oral Drug Delivery System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harmaceutics. 2023 Feb 1;15(2):484. doi: 10.3390/pharmaceutics15020484. PMID: 36839807; PMCID: PMC9960885.
[6] Pardeshi CV, Belgamwar VS. Direct nose to brain drug delivery via integrated nerve pathways bypassing the blood-brain barrier: an excellent platform for brain targeting. Expert Opin Drug Deliv. 2013 Jul;10(7):957-72. doi: 10.1517/17425247.2013.790887. Epub 2013 Apr 16. PMID: 23586809.
[7] Huang Q, Chen X, Yu S, Gong G, Shu H. Research progress in brain-targeted nasal drug delivery. Front Aging Neurosci. 2024 Jan 17;15:1341295. doi: 10.3389/fnagi.2023.1341295. PMID: 38298925; PMCID: PMC10828028.
[8] Ikeda T, Kawabori M, Zheng Y, Yamaguchi S, Gotoh S, Nakahara Y, Yoshie E, Fujimura M.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Derived Exosome Alleviates Hypoxic-Ischemic Brain Injury. Pharmaceutics. 2024 Mar 23;16(4):446. doi: 10.3390/pharmaceutics16040446. PMID: 38675108; PMCID: PMC11053690.
[9] Tareen FK, Perteghella S, Catenacci L, Ghiozzi G, Cama ES, Robustelli Della Cuna FS, Sorrenti M, Bonferoni MC. Carvacrol-based nanoemulsions loaded with dimethyl fumarate intended for nose to brain delivery for treatment of multiple sclerosis. Drug Deliv Transl Res. 2025 Jul 5. doi: 10.1007/s13346-025-01912-x.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617997.
[10] Veronesi MC, Alhamami M, Miedema SB, Yun Y, Ruiz-Cardozo M, Vannier MW. Imaging of intranasal drug delivery to the brain. Am J Nucl Med Mol Imaging. 2020 Feb 25;10(1):1-31. PMID: 32211216; PMCID: PMC7076302
[11] M. Agrawal, S. Saraf, S. Saraf, S.G. Antimisiaris, M.B. Chougule, S.A. Shoyele, A. Alexander, Nose-to-brain drug delivery: An update on clinical challenges and progress towards approval of anti-Alzheimer drugs, J. Control. Release 281 (2018) 139–177
[12] Qiu Y, Huang S, Peng L, Yang L, Zhang G, Liu T, Yan F, Peng X. The Nasal-Brain Drug Delivery Route: Mechanisms and Applications to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MedComm (2020). 2025 Jun 6;6(6):e70213. doi: 10.1002/mco2.70213. PMID: 40487748; PMCID: PMC12141948.
[13] J.J. Lochhead, R.G. Thorne, Intranasal delivery of biologics to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dv. Drug Deliv. Rev. 64 (2012) 614–628.
[14] 郑淇文,高静,梅蕾蕾,等.美国FDA批准鼻脑给药相关的鼻喷雾剂说明书分析[J].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23, 40(20):2872-2877. DOI:10.13748/j.cnki.issn1007-7693.20232527.
[15] 戴学栋,孙涛,黄芳华,等.改良型新药非临床研究的一般考虑及需要关注的问题[J].中国新药杂志, 2017, 26(18):7.DOI:CNKI:SUN:ZXYZ.0.2017-18-002.
[16] 江芝,刘学武,姚芙,等.鼻腔给药制剂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的一般考虑及挑战[J].中南药学, 2025(5).
[17] Merkus FW, Verhoef JC, Schipper NG, Marttin E. Nasal mucociliary clearance as a factor in nasal drug delivery. Adv Drug Deliv Rev. 1998 Jan 5;29(1-2):13-38. doi: 10.1016/s0169-409x(97)00059-8. PMID: 10837578.
[18] Forbes B, O'Lone R, Allen PP, Cahn A, Clarke C, Collinge M, Dailey LA, Donnelly LE, Dybowski J, Hassall D, Hildebrand D, Jones R, Kilgour J, Klapwijk J, Maier CC, McGovern T, Nikula K, Parry JD, Reed MD, Robinson I, Tomlinson L, Wolfreys A. Challenges for inhaled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Induced alveolar macrophage responses. Adv Drug Deliv Rev. 2014 May;71:15-33. doi: 10.1016/j.addr.2014.02.001. Epub 2014 Feb 13. PMID: 24530633.
[19] Zhang X, Xia J, Zhang W, Luo Y, Sun W, Zhou W. Study on pharmacokinetics and tissue distribution of single dose oral tryptanthrin in Kunming mice by validated reversed-phase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ultraviolet detection. Integr Med Res. 2017 Sep;6(3):269-279. doi: 10.1016/j.imr.2017.05.001. Epub 2017 May 25. PMID: 28951841; PMCID: PMC5605383.
[20] Li C, Yao S, Li Z, Gao Y. Application of Novel Drug-Delivery Strategies in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dv Mater. 2025 Jun 9:e2503646. doi: 10.1002/adma.202503646.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489094.
[21] 孙搏;陈桂良;徐瑛;鼻脑递送给药治疗药物的临床应用研究现状[J];中国现代应用药学;2025年08期。
[22] https://doi.org/10.1021/acs.molpharmaceut.3c00588
版权声明:本文来自鼎泰集团内容团队,欢迎个人转发分享,谢绝媒体或机构未经授权以任何形式转载至其他平台。
免责声明:本文仅作行业信息交流而非医疗广告非商业盈利之目的,内容仅供分享学习。本文也不是治疗方案推荐。如需获得治疗方案指导创利配资,请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发布于:江苏省公富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